帝国晚期的宗族社会与日常政治
With: Michael Szonyi
Date: Aug. 19, 2022
林永青:首先我们欢迎宋怡明教授,谢谢您能够接受我们价值中国的访谈,非常高兴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,谢谢。
宋怡明:很高兴跟价值中国进行交流,可以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,非常荣幸。
林永青:首先第一个问题,我们知道您最近出版了一本中文新书,英文的书可能以前已经出版了,最近应该是中文版的新书《实践中的宗族》。我了解本书有关明清时期福建地方志的相关历史内容。想请您展开谈一谈这一研究主题,福建地区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与宗族组织的一个社会变迁。这是一个偏向于人类学的问题,还是历史学的研究?
宋怡明:实际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恰当,可以说两方面都是。我在中国历史学术界被认为是属于一个所谓的“历史人类学派”,就是所谓的“华南学派”的另一名称。这本书的出版,首先要说我非常高兴,出版过程相当漫长。我一个朋友也是同事,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王果,花了很长时间很多力气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,但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拖了很久,在终于这几天要正式出版。这本书是我大概差不多30年前,从我的年轻时代(头发还是黑的)时所做的博士论文而发展出来的。英文版已经是20年前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的。
因为当时可能国内的学者觉得本书不太值得翻译,但是后来我成为了哈佛的教授,也作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,突然间,中国学术界认为,可能还是需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一课题,需要将本书翻译成中文。好的,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概括,中国南方的家族组织是众所周知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结构,一种社会组织,但是一般地,南方人也好,北方人也好,大概都有一个理解,认为是家族制度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制度。
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我们在南方如福建广东地区所看到的家族,包括今天所看到的家族制度。当然,比照中国5000年的历史来讲,家族史只是很短的历史,不会超过600年。
我这本书就是想要解释家族组织的发展,用一个趋势或者一个地方,用微观-微微观的的角度,去了解在某一个社区,某一个地方,某一个社会,为什么会有一个新的制度发展出来。
在这方面我是跟着我一个老师,厦门大学郑振满老师所指导的智慧进行学习。郑老师主要是研究闽南地区的地方史,我就在福州地区去观察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,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之下,才会有农村家族的发展。基本上本书要回答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。
回到你的问题,本书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都有。可以这么说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。虽然,人类学家会比较不接受这个说法,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宋怡明“不太了解什么是人类学”(笑)。
但是,我要强调的一点是,这本书是利用我们所说的一个历史人类学的基本方法,换言之,“田野调查”的方法。本书与其他研究中国历史的书最大的不同,就是我的研究中有很大比重,采用了田野调查。
林永青:了解,谢谢。还有一个比较学术些的问题,我想做一些区分:可能只有中国的读者会了解,在英文里面书名叫KINSHIP的这个词,可能会翻译成”家族”或“亲属”,但是中国有一很特殊的事物叫做“宗族”,这跟家族还不完全一样、或者很不一样,对吧?
中国有传统上有所谓的祖先崇拜,所以才会有家族传统。当然一个家族更大了以后,比如说是同姓的家族——我们是姓林,你在福建你就知道最大的两个姓,一个姓林,一个姓陈,“陈林半天下”——所以才了有所谓“宗族”的概念。
那么据您的研究,您认为中国或者说特别是在福建地区,宗族的特点跟西方,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上所研究的家族,有哪些大的差异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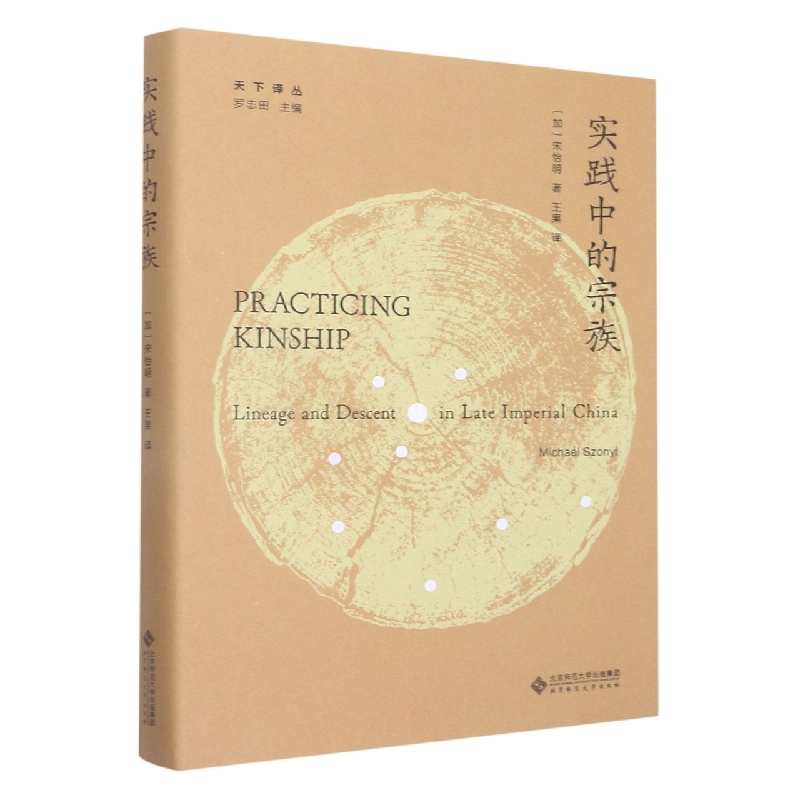
宋怡明:你的问题包括很多细节,我很感动,你很详细地去理解了我的著作。
我觉得,大概从两个角度去谈这个问题,第一个是在历史上不同的社会都会出现了家族组织,然后,家族组织的社会功能,在不同的历史环境,不同的社会状况都会起了不同的作用,不同的功能。
而且,家族是一个跨区域的概念,很多地方都可以有kinship,但是中国的kinship的一些特点,尤其是南方,就是它的社会功能很完整的,比如说在我们福建很多“单姓村”,整个村就这一个姓。
只有一个姓,都是在他们的历史印象中——全村的所有人,(当然另外一个女性是要嫁进来的),所有的男性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。
还有一条。就是社会网络,社会关系非常的密集,非常的紧密。Their social ties are extremely dense。所以宗族在很多领域,文化领域、教育领域、政治领域它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还有一个区别是,中国的比较特别的,就是你说的祖先崇拜的传统,中国可以说有一个强大的宗族思想,就是亲属关系的背后有一个知识的逻辑,有一个强大支撑,有一个ideological background。
我们如果要了解历史,说历史的种族,历史的家族,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因素,一个风俗的因素,思想的因素,一个族裔的因素,跟现实连接起来,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么复杂的一个关系。
林永青:说到传统,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——你刚才谈到说您的祖籍是在匈牙利。匈牙利有一个跟中国很一样的特点,(但我没有具体研究过),就是西方很多的国家或者说几乎所有区域都是人名的“名在前,姓在后”。名是first name, 姓(surname)是last name;只有中国和匈牙利,是“姓在前,名在后”,这体现了对家族的重视和尊敬。
宋怡明: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发现,这个重大的发现,我还没考虑过的,我没有意识到。
林永青:对,有研究者认为,匈牙利可能跟中国传统上的北方匈奴民族有一点关系,但是,我没有做过匈牙利研究,所以我不能确认。但是,您刚才谈到的宗族社会,可以肯定的是,中国人特别认为是家族和祖先很重要,所以姓放在前面。
宋怡明:是的,我不能确切地回答你的问题,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意思的话题。
我做一个猜测,我们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讲,可以发现姓氏的出现是一个比较晚近的现象,很多学者都认为是,当国家在想办法来登记所有居民时,才会有姓氏出现。历史研究表明,1000年或者2000年以前,在欧洲的很多地方,非洲的和中东的很多地方,都还没有姓氏。
应该是帝国或者王国的出现后,才会发现姓氏的踪迹。另外,说不定那些姓放在前面的种族,是否为比较早出现的国家跟老百姓的关系的一个过程。当然,这完全只是一种猜测。谢谢。
林永青:我们也预祝您的书在人类学历史学这个方面,对中国研究会有更大的影响跟帮助。
宋怡明:这个问题我可以再插一句吗?刚好这个礼拜对我个人的出版,是一个很大的时刻,宗族的那本书拖了好久才翻译好的的。然而,这个礼拜却还有一本书也要出版。
就是中国问题的一本书,包括中美关系的洞察。我们在前几年,为了庆祝费正清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建立60周年,我们出了一本《中国36问:对一个崛起国家的洞察》。这本书蛮受欢迎的。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,所以我们的编辑和学者,决定出版这样一本书,这本书是多篇短文章的汇集,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讨论中美关系中一些很重要的专题,现在,我们又出版了中文版,所以我也特别推荐给你们的读者。
林永青:太好了,我们很乐意帮助费正清中心的相关中国研究做些宣传。您刚才谈到费正清研究中心,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。我们知道这应该是在世界著名大学里面,研究中国问题最早的一个中心。这里,又讲到一个跟福建相关联的事情,费正清当时跟一个中国很著名的女学者,就是林徽因家族有很多的联系对吧?也有很多的私人交往。所以我就特别关心,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方式是什么?是邀请一些学者去做研究还是怎样?另外,中心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?
宋怡明:我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讲,我们费正清中心是他本人在50年代建议下建立的,当然当时并不叫“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”这个名字。费正清本人退休后,他就让傅高义接任中心的主任,然后名字就改成了今天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。
林永青:傅高义就是当年写过《邓小平传》的那位学者?
宋怡明:是的,就是那一位,他也是我的一个指导老师。
当时在美国很多学者都认为美国需要进一步的从社会科学,或者从综合的角度了解中国,你可能也会觉得是一个敏感事情——这与冷战时期的对手研究,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费正清本人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学者,这也是他之所以能集中了很多资源,让哈佛大学校长许可了建立这么一个中心。
我经常开玩笑说,当时我们美国的学者都觉得,需要进一步的了解“中国的解放”是怎么一回事,亚洲其他国家也将发生怎样的形势变化。然而,我们现在冷战结束了数十年,中美关系建交也已经几十年了,我们现在当然已经脱离了政治影响学术的很深的一个时刻。目前,可以说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,成为了哈佛大学跨学科中国研究的脑库。
我为什么说脑库?而说我们不像智库,一个原因是,我们更多是在做学术研究,另一原因是,我们不是为了国家,不是为了政府,不是为了其他什么机构进行研究,我们是一个集中所有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的专家,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。我们的在世界的名气是不完全靠中心本身,而是靠我们这个团队。
就是哈佛大学集中了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伟大学者,我们中心是一个以服务为主的中心,我们用了几个方式来支持哈佛中国研究,首先是教育。第一,我们培养学生,我们支持哈佛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等等,我们也支持中国研究学者。第二,我们进行学术活动,包括会议、演讲等等工作坊等等。第三,我们设立了一个图书馆,一个资料库,这个资料库,我可以冒昧的说,是研究现代中国的全世界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,很多学者都会跑到美国,跑到波士顿,跑到我们哈佛去查资料,我们也进行很多学术交流,比如说我们每年就接受了几十个访问学者。
从2020年疫情以来,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。我觉得在2022年我们新的任务,是尽力保持中美两国间的关系,在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的当下,我们应当有一个新的责任。这也一个非政府的关系和沟通渠道。
我们还从事一些我们叫做“中国与世界”的研究。之前的中国专家,只需100%的研究中国;但是现在在中国已经崛起了,我们如果要了解中国,我们需要了解中国跟其他地方的关系,与世界的关系。我们要了解中国在世界不同领域所起的作用,很显然的一个例子:就是中国研究不能跟气候变化研究完全分开,在我们今天的世界,任何地方也不能把两者分开。当然,这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。
第三个方面是所谓的公共教育,帮助普通美国公众了解中国。明白中国现在这么的重要,所以我们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,包括我刚刚提的出版那本书,包括社会媒体等等,来让美国的观众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中国。
林永青:我以为,各国的主流媒体都认为美国公众以往对于美国以外的世界,并不太关心。而现在,由于互联网和经济等主要因素的影响,世界已经越来越一体化,他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。
宋怡明:可以这么说,但是也要从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:之前我们上一代的学者,会觉得他们的责任就是做学问;这当然是最重要的,但我觉得在目前的世界,我们的学者,我们的专家有另外一个责任:就是要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参与贡献。
林永青:我很同意您刚才对“脑库”的一个定义和理解。接下来可能是一个哲学问题,我个人特别感兴趣,因为您当年求学的时候,特别从哲学系转到了历史系,这是出于什么原因?当时期,应当冯友兰的著作对你影响很大?
宋怡明:这是个有趣的问题。我在台湾读哲学本科哲学专业,本科生一年级时,我们的课本就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。
林永青: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应当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。
宋怡明:在台大读书时,我还是一个普通的本科生,所以我们的课本是中文版,但是我还买了英文版。
你这个问题很可以从一个很抽象的角度去谈,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谈论,因为我不是那种讲思想史的学者,我只好从我个人的背景去谈这个问题。
我转了专业大概主要有两个原因,一个我是80年代开始学中文,开始跟中国的学者及中国学术进行交流。80年代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很根本转变的一个国家。当时我觉得如果想理解其转变背后,以及转变的一些影响,而哲学是比较不适合讨论这些问题。我当时有这么一个感觉,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,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去谈起的。
另外,我是一个很喜欢跟朋友交流的一个人,这是我个人的性格,我喜欢与中国的同事,华南历史学派的学者,跟中国各地的老百姓交流采访,交朋友。对的,这是我个人的性格比较喜欢的,远远的超过我在图书馆看哲学的兴趣,所以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。
林永青:对的,哲学应该是一个更抽象,或者说是一个离社会现实更远的东西。
宋怡明:更远的,没错。
林永青:了解,尤其在中国,因为有很长时间的历史,而且也有很长时间的对于历史的记录。这可能是全世界最长的历史记录了,对吧?从司马迁那个时候就开始记录历史了。之后,历朝历代,都有官修和民间的历史纪录留存下来。
宋怡明:中国历史是一个无底洞,有很多很多的题目可以配套,对的。
林永青:我也认识不少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,这个学科被叫做汉学sinology。您怎么看待这个学科的?我个人总感觉这个词好像不那么恰当。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的,很多的媒体也好,学术界也好,就认为您是一个海外的汉学家。
宋怡明:这很有趣。社会媒体给我叫做是什么汉学家,我不在乎,但是我自己个人不认为,或者我不会自己说我是汉学家,为什么?
因为汉学家这个概念有一个潜在含意是,中国的历史,中国的文化,中国的哲学是跟世界的历史、世界的哲学,世界的文化是......
林永青: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是割裂的(separate)是吧?
宋怡明: Separate,是的。所以你如果问我,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者,我都会回答说,我是一个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者。
我完全同意你的判断,但是我还补充一句,我觉得在汉学家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,因为现在美国很多所谓的中国通China Experts,然而,他们可能名不符实,所以还需要汉学家这么一个角色。
比如,他们不懂中国的中文,在中国也没呆过。他哪里就可以做一个中国专家,如果那些中国专家来指导美国对华政策,我们美国就真的完蛋了(笑)。
林永青:完全同意,因为如果你甚至都不了解一个语言,你是没办法做非常具体跟深入的研究的。
宋怡明:你也没办法自然而然的跟当地人交流。
林永青:接下来一个问题,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的一本很著名的书《文明的冲突》(Civilization Conflict)。您曾在一文章当中提到过说,“所谓文明的冲突没有太大的意义”,我个人也是这个观点,所以我马上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也就是说您认为,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冲突,应该主要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。还有一个背景补充,我恰恰是从冯友兰那里借鉴来的,冯友兰有一个观点,他认为没有所谓different的civilization文明,但是有different的culture文化。我就认为,文明应该会是趋同的,比如,世界都会朝着一个比如说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方向。
所以我认为文明是有所进步的,不能陷入在所谓的相对主义里面,显然是不对的。
所以文明是有进步与落后差别的,而文化可以有不同的特质。这是我的理解,我想听听您的意见。
宋怡明:这个问题说实话,怎么回答都有点尴尬的感觉,为什么?因为是亨廷顿是一位伟大的学者,我这么直接的反驳批评他,有点不太自然,但是我总是觉得他的观点“文明冲突理论”,是怎么说也不到位。
当然可以从一个学术的具体角度去谈,比如可以将问题转换为,世界的不同文明的界限要划在哪里?或者是,世界的每个文明的内部分化是怎么样的等等,这就很具体了,避免全面地否定他的理论。
林永青:还有,我觉得也存在历史的断代问题,带来的文明问题。
宋怡明:对,也有历史的断代问题等等,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通俗的角度去谈,我和我的中国朋友,我的中国同学,我们的中国同行,我们之间的共同的地方,远远超过了我们不同的地方。大概我是当了父亲以后,才真正的意识到这一点。我对我孩子的忧虑,我对我孩子的担心,我对我孩子的期望,相信跟你是完全一样的。
林永青:跟中国家长的担心和期望,是完全一样的。
宋怡明:更准确地说,“我们如果不谈政治,我们就不会有冲突”。我们可以很好地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,都没有冲突,所以这是一个很小的却很好的证明。至少,文明冲突不可能是一个很完整的解释。It doesn't correspond to the facts。
另外,我觉得对于我再补充一句,我觉得他那本书之所以怎么受欢迎,也许是跟后来美国跟中东的冲突有关。
林永青:尤其是与911前后的一些背景有关。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更加激烈。
宋怡明:你认为是911事件,我们也可以从美国在中东的“帝国主义行为”去谈。但是这样子谈,美国人会不爱听。如果说美国在中东没有犯错误,就只能说成是文明冲突,it's excuses,American way。
林永青:下一个问题就是谈到您对于历史的研究方法,也是您很推崇的研究方法,你就曾经说过,“要了解这个百姓才能了解中国”,所以想请您谈一谈,在研究当中的你所理解的“小历史跟大历史”的区别。
宋怡明:好,我觉得我了解“老百姓的小历史”,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因素,一个是所谓的“底层历史”来谈,第二个是所谓的“微观历史”。
第一个是底层历史,bottom of history,这是大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引起的一个历史观点,认为历史上总统的皇帝的故事不是整个历史的全貌。我们不能只以那些领导人的谈话,他们的行为,作为一个很完整的历史的例子。
林永青:对,我也插一句,今天的历史不能只关注领导人物的历史。当然,中国的传统历史也只有帝王史,包括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与全部的《二十四史》也只有帝王史,没有什么百姓和社会什么事。
宋怡明:没错,这跟西方历史一样的。有趣的是,中国历史也好,西方历史也好,两者对传统历史观的不满,是差不多是同时间引发的,尤其是在中国,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有密切的关系。
第二个是所谓的微观历史,微观历史的意思说,我们如果要了解很大很重要的历史现象,也可以在很小的地方发现出很大的问题。所以,我的基本的历史观,就是这两个概念的结合。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去谈历史,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。
而且,从不同的历史观出发,我们如果研究老百姓的历史,我们对历史的论述会很不一样。
林永青:这里有一个立场的问题,也有一个观察角度的问题。
宋怡明:就是说,老百姓的历史,不但补充了验证了帝王的历史,也会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历史。
林永青:我稍微做一下summery,其实有一个问题是叫做以小见大,或者用一个中文成语叫做“察微知著”。英文解释是to examine the tiny clues to know general trends。
这还有一个论述完整性的问题,对吧?一个多维度或更全面性的问题。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您之前的一本书《被统治的艺术》。那么,在这本书当中,你提出了所谓的"日常政治",我不了解您用的词是daily politics还是civil politics。
宋怡明:我用的词是everyday politics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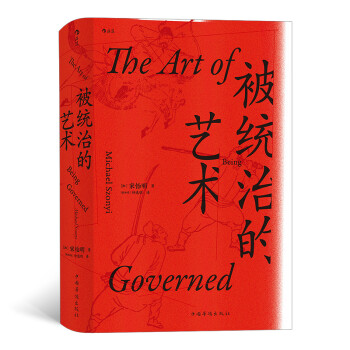
林永青:everyday politics,所以听上去比daily还要daily(笑)。还有一个关于“制度套利”的问题,就是说“普通的老百姓怎么去做制度套利”。我想补充一点,“老百姓”也是中国很特殊的一个词,你在英文里面你找不到一个词叫老百姓。
宋怡明:估且译为百姓Hundred Surname对吧?但是其实我不确定,因为以我有限的对西方历史的理解,很多的国家在历史上,普通人是不能够有姓的。
林永青: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,只有贵族有姓。但是在中国,百姓已经变成一个普通人average people的概念。所以,想请你谈一谈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跟制度套利的一些关系。
宋怡明:我要先强调日常政治,这不是我发明的一个概念,其他的学者已经提到了日常政治,我们现在讨论,是因为这跟我们前面的讨论话题很接近的。
我们之前传统的学传统的历史学者认为政治是什么?政治是皇帝跟大臣们在朝廷讨论国家的政策,或者外交问题等等,但是实际上,我们所有的人天天碰到很多政治的问题,比如说在传统的经济,传统的社会,日常政治主要指的是老百姓接受双重或多重挑战,来自生存环境的,来自当地政府的。当然对老百姓最主要的资源是他所种的地,他是靠什么吃饭的?有关那些资源的控制与分配。
生产资源从哪里来的?我种田,要向地主缴多少租金,国家要收多少税,这些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政治问题。他们怎么适应,他们怎么面临这些问题,对他们来说,没有更重要的政治问题了。
“制度套利”的概念,我觉得比较自豪,制度套利虽不是我发明的一个词,它是从金融学应用的一个字,但是我把“制度套利”移植到历史研究,这是我的一项贡献,所以在这方面感觉很自豪。
我估计你们的价值中国的很多观众,都是金融界或者经济界的背景,所以他们对制度,套利,监管这些概念,肯定不会陌生。制度套利,就是指利用不同的监管制度,或者不同监管制度之间差异,进行的套利行为。
实际上我大量读了你们福建人,特别是很多福建的明代的族谱,我就发现族谱里面有一些记载,说明当时的老百姓并不比今天的银行家今天的老板水平差,他们非常的聪明,采用种种方法,种种策略,来利用当时那个制度所遗漏的规定,或者不同制度的差异,来套利。
很多人说这个制度套利,是中国老百姓是太狡猾了,我并不是这个意思,我的意思说普通老百姓虽然没有读过书,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,但他在日常政治中运用策略非常的娴熟。
林永青:sophisticated
宋怡明:是的,他们的策略非常的sophisticated,非常的成熟。
林永青:因为你刚才讲到福建的普通的老百姓,其实我原来还有一个问题,后来我拿掉了,我想再拿出来问,因为你也在研究所谓海外华侨,海外华人的历史,对吧?
那么,最多的海外华侨就是来自两个地方,一个是福建,一个是广东。包括当年孙中山策动反清革命时,大量的参与者都是福建人或广东人,对吧?
你刚才又谈到关于制度套利的问题,还用了一个词叫sophisticated,所以,今天的海外华人当中大量的也是广东人跟福建人,他们可能是很多代以后的移民了,他们在今天如何在移民目的地国“套利”呢?
不知道对这个海外华人华侨的问题,您的研究重心是什么?
宋怡明:实际上我没有做这个海外华人的研究,我原来是很想做一些的,但是后来没有做成,因为中国国内有太多的好题目,所以我就把这个题目先放一放。
林永青:好的,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。
我看到过有人将《被统治的艺术》一书,称为叫福建版的《百年孤独》。他是个音乐人,就是高晓松。我们在一些场合有过交集。
马尔克斯写作《百年孤独》的时间,大概是20~30年前了。这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(magic realism),所以我就不很理解,因为你的书是一本研究历史的书,为什么被作了这种类比。你的书中,“魔幻”在哪里?这里的“隐喻”又是什么?我很有兴趣。
宋怡明:高晓松这样说当然很容易理解的,作为老朋友,他在帮我做宣传,他要让我多卖卖书,所以他才做这个类比。但是,确实我还是要回答你的问题。我那本书跟魔幻现实主义怎么类比?高先生是聪明人,他不会乱讲,我觉得大概两个可能性,其一,他的意思说,这本书真的是一个杰作,一个masterpiece,okay,我对那本书也可以说是很满意,但是还不是一个masterpiece,还不是杰作。这本书在历史领域比较特别的一点,就是我每一章是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,我估计高晓松几十年都没有读多少历史了,他所懂的历史都是那些老一套很无聊的,这个皇帝那个皇帝什么的,所以他看到这本书的每一章开头都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,他也会觉得很新奇。
其二,我猜测高的历史性格,跟我的历史性格是很一致的。2019年底,我的出版社是中国一个非常好的出版社,他们计划了非常好的宣传,结果因为疫情没法如愿。但是,我还是用一秒钟做宣传工作,这本书确实故事很多,故事很好玩,读者可以赶快去买一本没问题的。
林永青:我们也可以用一分钟帮你来做宣传(笑)。我再回到刚才讲的,我认为历史是充满了隐喻的,包括现实也充满了隐喻。最近很流行的元宇宙METAVERSE概念,也是从隐喻开始的。METAVERSE这个英文词的词根,与隐喻METAPHOR有相同前缀的,相信不是巧合。我个人作过一些研究,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诸多大科学家,都认为想象力-隐喻-类比这些东西,比单纯的知识更重要。
比如,我们最近和数字孪生(DIGITAL TWIN)之父Michael Grieves教授的交流,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类比,“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”,就是针对“信息-数据”这一对概念进行的类比,来进行的技术创新。人类可以理解“信息”,而机器专门处理“数据”。
宋怡明:你关于隐喻与创新的讨论,很有意思。类似,所以很多人认为我这本书《被统治的艺术》的主题是明代社会的在今天的某种隐喻。但我的本意可能没有那么tricky,毕竟历史变量太多了。有兴趣的读者,可以去买一本书自己来体会后面的隐喻是什么,哈哈。
林永青:那么您最近的研究的 focus重点会是什么?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研究的那些学者,特别是对海外的那些学者,您有什么建议?我比较希望了解。
宋怡明:好的,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。从我从工作的角度来讲,我最幸运的两个地方,一个就是80年代,在这个中国保持无限希望的改革开放的刚开始年代,。我跟你一样,我们都是跟改革开放成长了,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。
第二个的幸运,来自我的博士导师: 我在牛津大学读博士时,我的博导老师是著名学者科大卫David Faure。科大卫教授说,你不可以专门跟海外学者交流,你一定要跟中国的学者打交道,因此我很早就离开牛津到了中国。然后跟我刚刚提到的几个老师,郑振满老师、杨国桢老师,厦门大学这几个了不起的学者开始打交道,我经常开玩笑说,我为什么能有了哈佛的位置,是作为我们厦门大学或者是整个华南学派在美国的代理人, I'm the agent for 华南学派 in America。So what the advice,很简单,一定要跟中国的学者,不论你什么学科什么专业,要跟国内的学者打交道,多交流。
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我很简单的说两句,我现在有两个课题我非常兴奋的去做,所以我卸任费正清中心主任之后,我高兴地说的,我现在可以专门的去搞这两个课题。第一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,我正在写一本书叫做《中国农村现代史》,什么意思?就是从农村的经验,农村的角度去谈今天的中国现代史,这是第一个课题。
第二个是一个比较学术的,我希望是可以做成一个bestseller(学术畅销书),可以吸引到很多人去读。我跟我厦门大学的同事,我们在一个离福州不远的地方叫做永泰,发现了大量的民间文献。主要是明代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契约、族谱、账本等等,我要通过那些文献来写一个专门的《农村经济史》。
对,基本上现在重点是这两个研究项目,这两个课题如果做得好,需要长期在中国国内,所以我一直在期待疫情能够尽快复苏正常,我就有机会跑到跑到福建去田野调查。
林永青:太好了,土地问题跟农村问题的确非常重要。事实上,中国政府每年的中央会议的一号文件,就是关于三农的问题。
宋怡明:实际上,我这两个课题都跟三农问题有关的。我们共同期待。谢谢。
